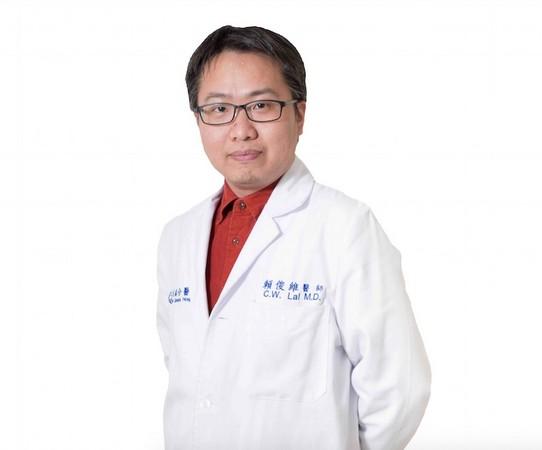
1944年春天,冀中抗联会的罗云和几位同志来到大清河西容城县西北阳村,住在一户张姓老乡家。此时罗云有孕在身,身体疲弱不堪。成天呕吐吃不下饭。
这家老太太看着很心疼,叫罗云不要再走了,就住在她家。罗云怎样推辞,老太太都不干。她说:“我正缺个闺女,你当我闺女吧,我就愿意看年轻人生小娃子,这年头添人进口才好啊!”
她太清楚了,老太太年已七十,何止缺个闺女,她缺的人多了。人们背地里喊老太太家是“三寡妇家”,屋里老少四辈只有四口人,曾祖母、祖母、母亲和一个独生子。
老太太丈夫很早就去世了,留下一个儿子,儿子也壮年早逝,留下一个孙子,孙子长大娶妻生子,有了一个儿子,这就是第四代了。一家五口人本来还过得去,不料飞来横祸。鬼子来“围剿”,孙子因穿着一件被媳妇洗得发白的衣服,被鬼子认定是“八路”,杀害了,全家三个寡妇就守着一根独苗生活。
老太太每天早晨都给罗云煮两个鸡蛋。蛋是那个年月每家的宝贝,要拿去换油盐、针线的,罗云不忍心,但老太太坚持要她吃下。
有一天,老太太带着点兴奋地小声告诉说:“我后面里还藏着大枣和粘米,过一个月有了苇叶,我包粽子给你吃。”
因为工作关系,罗云不久去了别的地方。出门时,老太太反复说,端午节要来啊,我包粽子给你吃。罗云点了点头。但到了端午节,罗云并没有去老太太家。有同志告诉她,老太太逢人就问:“罗到哪里去了,怎么不来我家呢?告诉她,她不来,我家不吃粽子。”
端午节过后,罗云和同志们恰巧又转移到西北阳村。到达的第二天,老太太提着一篮子粽子来了,进门后作古正经告诫男同志,你们只能吃两个,其他的都给罗吃,她要生娃娃。大家哄堂大笑,真是个操碎了心的老妈妈。
9月,罗云临近临盆。同志们把她安排到雄县、任丘交接的一个地方,叫杨家场,这里相对安全。她住在一个军属家中,这家是任丘大名鼎鼎的抗日绅士高士一的侄媳妇。高士一率家乡子弟随贺龙师长走后,敌人烧掉了他们的房屋,高家人就分散隐蔽在这一带。
10月,罗云的女儿出生了。她给女儿取名杨平地,希望将来她少一点坎坷。可是,这个在民族苦难中降生的孩子,从出生之日起,就卷入了残酷的斗争,命途艰险,生死难卜。
这年旧历12月25日,寒风凛冽。拂晓,敌人偷袭杨庄。地委机关和群众来不及转移,全下了地道。地道土质是沙性的,挖得又矮又窄,一百多号人在地道里爬着走。罗云带着两个月大的孩子也挤在人群中。
下地道的人有些是重伤员,群众也多是老弱病残,战斗力弱。地委领导决定,隐蔽目标,静观其变,伺机转移。
可能是受了惊吓,罗云的孩子自进入地道,就不停地啼哭。罗云很着急,她想了办法,可没法让孩子止住哭声。丈夫在一旁悄声说,这里有通气口,不能让鬼子听到,必要时......
丈夫没说下去,意思罗云很明白,她声音低沉地回了声:“知道了。”边上的同志们和老乡们,彼此看了看,都没说话。
孩子还在哭。罗云的手伸出来了,放到了孩子的脖子上。这时候,有人低声喊了句:“慢着!”一双手拉住了她的胳膊,那个声音颤抖着说:“快,给她奶头!”罗云如梦初醒,赶紧塞给孩子奶头,孩子果然不哭了。
她感激地回头一看,说话的是房东杨大娘。杨大娘又递给她一件棉袄,要她盖着孩子:“蒙上头,用手支着点。”
罗云带着孩子往前走了几十米,这里离地道口远了,上面的声音听不到了。杨大娘过来给她一个馒头:“吃吧,吃了这个好生奶,要不她又得哭了。”这是大娘下地道时拿的两个馒头中的一个,罗云感激地接过来,三两口吃下了馒头。
观察哨报告消息小儿聪慧符,敌人在到处抓人,在提水做饭,在宰杀抢来的鸡和牛。地委负责人杨英分析,敌人今晚驻杨庄,估计明天就要挖地道了,今晚必须突围。
干部会议开过,突围选择在村南边坟地里最新开挖的一个地道口。民兵侦察,敌人并未发现这个地道口。突围马上开始。民兵在前面开路,带武器的同志负责断后,妇孺老弱在中间。
罗云右胳膊夹着孩子,左手托着孩子的头,用双膝和右手在地上爬行。洞太窄了,每走一步都要磕下很多土。
虽然是爬行,但队伍前进的速度很快。罗云有些担心的是孩子。前面还在哼哼唧唧地哭,只是声音有点小,但渐渐地,什么声音也没有了。罗云想到了揪心的结果,心里一阵比一阵发紧。但不论怎样,她得把孩子带出去,后面的人还要出去。
孩子衣衫单薄,因为不便行动,衣服都丢在洞里了,她紧紧抱着孩子赶路。杨大娘脱下棉袄蒙在孩子头上,自己只穿着小棉衣。罗云几次推辞,都被杨大娘挡了回来。她就说一句话:“别冻着孩子。”
大家都在急速赶路。走了好几里路后,罗云才发现大娘不见了,大娘家里人也不见了,她很懊悔,没来得及把棉袄还给她,这么冷的夜,她怎么过啊。
孩子真像睡着了,一直没有发出声音。走了二十里路的样子吧,到了一个村庄,大家都有些累了,决定进村休息一下。罗云摇了摇手中的孩子,她没动。一个感觉越来越强烈,这孩子不是睡着了,而是......
屋里很暖和。桌上亮着一盏小油灯,一个妇女睡在炕上。女人看见罗云进来坐了起来,先是愣了一下,然后马上穿衣过来,从罗云手里抱过去孩子。
灯光下,孩子的脸青紫,四肢挺直,应该冰一样凉。罗云看着女人脱下孩子又冷又湿的衣裤,抱进被窝,又把孩子抱在怀里,忘了自己该干什么。
过了好一会,“哇”的一声哭从被窝里窜了出来。女人欣喜地喊:“好了,这下好了。”罗云好像才恢复了知觉,只感到浑身散了架似地疼。
吃过饭,一起过来的同志要连夜去河西。但这一对夫妇说什么也不让罗云走,要她和孩子在这里先休息。在交谈中知道,这家男主人是本村农会主任,参加过抗联的学习班,认识罗云。
因为深感带着孩子不便工作,也非常不安全,罗云想把孩子寄托出去。好几个大娘大嫂帮她物色有奶有可靠的人家,可一时找不到。
然而,敌情又趋紧张。这次杨大娘说什么也不同意罗云带孩子下地道,要他大孙子夫妻二人把罗云母女送到二十里外她女儿家去。孩子放在一个特制的圆筒棉袋里,保暖还好呼吸,就是有点重,连孩子一起有十来斤。二十多里路走下来,大半时间都是杨大哥在抱,气温零下十几度,他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却坚持不让罗云抱。
一天,她和区县妇联的同志在米西庄开会,突然接到报告,说一股敌人朝这个方向来了。罗云要带着孩子下地道,但王大娘不同意,只好由她带着孩子转移了。想到杨庄那次的教训,罗云有些担心,可王大娘却叫她放心好了。
地道一躲就是一天,晚上罗云心急火燎赶到米北庄王大娘家,一进门就看到孩子正躺在大娘怀里睡觉。大娘乐呵呵地说:“饱啦,睡着啦。四个妈妈的奶,吃得可好啦。”
在这些善良的人们呵护下,孩子天天在成长。可是罗云的身体出了点问题,紧张的工作和急躁的心情,让奶水骤减。
米东村烈士朱德声的父亲朱桐林大伯,听说了这个事情,专门把罗云接到家中,杀鸡熬汤帮她催奶。但罗云的心情却很糟糕。
奶水减少这事让她愈发觉得必须尽快把孩子托付出去,否则工作全耽误了,孩子也成了一个危险因素。她急得都哭起来了。
朱大伯和朱大嫂反复安慰她。朱大伯说,急什么,敌人不来,咱有山芋粥吃,敌人来了,咱们和你在一起。话是这么说,朱大伯为了宽她的心,已经到处托人在找合适的人。
朱大伯女儿传来话,说她们那里有一对夫妇,孩子不出月夭折了,夫妻俩很想养个孩子。罗云得到消息就要走,但正是大雪天,外面雪深不下一尺,出行十分困难。那时,为了斗争的需要,路都挖断了,变成了交通沟,大雪之下,路沟难分,仓促行走很是危险。但罗云坚决要走。
朱大伯考虑了好一阵,终于想出个办法:做拖床子。所谓拖床子,就是一种载农具下地的四方架子,没有轮子,靠牛拉向前滑行。
朱大伯在拖床子上搭上板子,铺上褥子,让罗云母女俩坐上去。拖床子走得慢,但是比走路不知好到哪里去了。不过看上去有点不伦不类,颇为滑稽。邻居见了没有不笑的,还说亏你坐得上去,这哪是人坐的,是放犁耙的。
朱大伯也乐了,回嘴说,这东西才好呢,坐着安全,倒了我一手能扶起来,“白脖子”见了,也不担心抢去拖枪炮。
路不好走。朱大伯在一旁吆喝着牲口,小心地察看地形,眉毛、胡子全结了霜,牛也穿着粗气。孩子偎依在罗云怀里,呼吸很平稳。罗云心里热潮翻滚,很不平静。
米北庄的王大娘来送信,说北庄有个产妇,孩子因窒息没有活下来,奶刚下来。罗云马上抱着孩子过去了。这家人很穷困,住着又低又小的草房,但夫妻都是忠厚人。
可是没过三天,王大伯就来了,说产妇高烧三天,很危险。罗云带着医生急忙赶过去,但药物缺乏,医生也束手无策。这个可怜的女人,两天后就因产妇热过世了。
大会结束时,已是夕阳西下。松了口气的罗云忽然想到离别多日的女儿,她几乎是脚不沾地地往八洋庄跑。
听到声音,冯大嫂一家十多口人从屋里全出来了,老人小孩每一个人都对她洋溢着盈盈的笑意,屋内孩子正安静地睡在炕头上。
补充:罗云,原名张云襄,曾用名张化一,河北省深县寺头村人。原天津市妇联执行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原中共天津市顾问委员会常委,中共十二大代表。
版权声明:本文为 “小儿收惊网,小儿辟邪小儿化煞宝宝平安符小化化病小儿夜啼符小儿聪慧符” 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 留言与评论(共有 条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