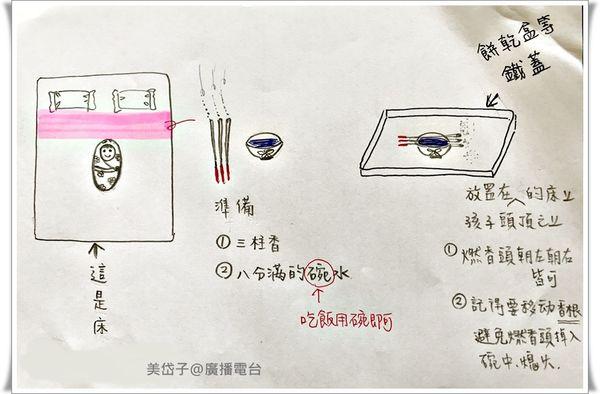
首先,自闭症是一个谱系(Autism spectrum),因此要精确定义自闭症是非常困难的。我打算说说我个人的一些观察和一个未完成的假说。我主要通过将自闭症中可以和面盲症对照的部分,将这两类认知缺陷作为正常人的两个极端来进行定性分析,最后根据 Jeff Hawkins 的计算模型建立一个简单的唯象概念模型。
需要明确一点,我在这里讨论的自闭症和面盲症都是狭义的,主要通过 Statistical Inference 的观点来定义的。为了给出这个定义,我选择了 Daniel Wolpert 建立的非正式术语。对于细节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 TED 的视频:
根据他的观点,大脑的认知能力主要是为了解决预测的问题。由于使用部分信息进行判断,大脑的预测不可能是完美的。因此,预测会存在两类问题,一类是假阳性(False Positive),就像狼来了这样的假警报;另一类是假阴性(False Negative),就是狼真的来了但是大家无动于衷。对于大草原上的人类而言(Evolutionary psychology),假阳性的危害要远小于假阴性。在涉及生存问题的时候,False Positive 只是增加心理压力和运动量——听到风吹草动就吓得逃跑了;但是 False Negative 则会危机生命——被草丛里面的蛇咬了可能会毒发身亡。需要指出的是,人类同时会犯这两类错误。
和理论计算和还原论者所关心的理想化问题不同,在自然环境中 False positive 并不全是有害的,一定程度的 False positive 有利于产生联想和归纳。人脑的 False Positive 倾向还可能促进了迷信和神话的构成,最终导致了宗教和部落的发展(金枝 (豆瓣))。Jeff Hawkins 的认知理论可以定量地解释这些现象,但是跟正文的讨论关系不大,因此我会在后面再讨论。
本文讨论的狭义自闭症,被定义为对 False Positive 的低容忍。很多自闭症患者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重复性偏好,以及只能在特定的环境下识别物体和他人。有兴趣的可以参阅一些高功能自闭症的自述,例如:
我是个面盲患者,经过我的长期跟踪调查,我也有家族病史。我对自闭症的兴趣也来源于面盲症的跟踪研究,因为有些人直接断定自闭症很多都是面盲症。从症状来说,这些描述是正确的,很多自闭症患者不能通过面部分辨他人的身份。但是我认为有必要区分这两种不同的面盲症。
首先面盲症的研究比自闭症少很多,最早关于面盲症的研究都是获得性的,而非遗传性的。其实两种面盲症的机制完全不同,有兴趣的可以去参考相关文献。有一个面盲患者花了很多时间来自己研究,他的网站有很多有用的信息:
我只想讨论我这种遗传性的面盲症,即几乎没有影响正常生活的先天性面盲症。大部分先天性面盲症都不知道自己有认知缺陷,因为这些患者的认知能力是健全的,通过各种补偿机制能分辨身边人的身份。大多数人都是因为新闻报道(互联网与面盲族的故事)才知道有面盲症,而真正能确诊的不多(不能分辨韩国明星的面部根本不是面盲症好不好,参考Cross-race effect)。
我的观点是,这类面盲症患者的认知缺陷和自闭症是相反的,他们对 False Positive 的容忍程度很高。以我个人为例,我并不是不能识别其他人,而是擅长于发现不同人之间的相似程度。换句话说,我经常会觉得其他人看来完全不同的面孔是相似的,我经常会觉得在人群中看到了熟人。但是由于这种错误让我对自己的判断能力失去了信心,最终我依赖其他机制来精确地识别他人的身份(在一个极端的情况下,我在咖啡厅里面仅仅通过声音正确识别了接近十年没有见过的一个前雇主)。
因此,这类先天性面盲症的特点是接受 False Positive小儿收惊符,因此他们的面部识别率很差,以至于他们放弃了用面部特征来识别他人。有些线索提到了面盲症患者的阅读能力较强,我个人觉得是有可能的。我只有很少的样本,包括我自己和直系亲属的下一代,他们和我一样喜欢阅读,能够自己编故事自娱自乐,会自言自语让其他人觉得很怪异。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来说,这些人脑洞比较大。
现在我建立了两个对偶的认知缺陷的定义,它们都是由认知能力相关的 False Positive 容忍程度所确定的。现在我可以做一些对比来解释其差异,它们对应的是一个典型的Continuum (measurement)(再随便找个轴就能凑龙与地下城的九宫格啦,不过就真的跑题了)。
跟据 Jeff Hawkins 的观点,我做一些简化和归纳(我说过,我是个面盲,就喜欢这个):大脑皮层在学习模式的时候总是在做归纳(Generalization),而大脑皮层在识别模式的时候却是在做细化(Specialization)。自闭症的刻板行为提高了 Specialization 的准确性,但是却降低了 Generalization 的适用范围。作为一个极端的例子,部分自闭症患者具有让普通人惊讶的记忆力(Eidetic memory),他们在画画的时候几乎是逐像素拷自己的看到的场景。我没有太多关于面盲症 Generalization 的证据,但是我很希望(wishful thinking only)我的音乐很糟糕跟我的认知缺陷有关系。
自闭症和面盲症都有面部识别障碍,但是他们的机制是相反的。对于自闭症患者,由于偏好细节缺乏归纳能力,他们会把同一个人当作不同的人来看待;对于面盲症患者,由于归纳能力强忽视细节,他们会把很多人当作同一个人来看待。
而对于一个没有认知缺陷的人而言,有正常的细节观察能力和归纳能力,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识别熟悉的人脸(在几百毫秒以内,这个我完全做不到,请参考N170),从而维持一个有效的社交圈子(受到邓巴数的限制)。因此,我可以推断,狭义的自闭症、正常人、面盲症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认知谱系。在这个谱系上,每个谱线上的个体对 False Positive 容忍程度都是接近的——而这是由一系列的基因型决定的表现型(有兴趣的请参考 Richard Hawkins 的The Extended Phenotype (豆瓣))。
我的假说可以这样归纳,对于正常人而言,认知能力中对 False Positive 的容忍程度在正常范围内,其基因的频率分布是稳定的(没有一个所谓的最优值,或者是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但是在其两极的边界上,其表现型会有一定的偏差,这导致了两种极端的认知缺陷,分别是自闭症和面盲症。但是不同的是,自闭症会影响生存和基因传播,而面盲症几乎是无害的。有意思的是,两种认知缺陷的频率是差不多的,都是 1%~2% 左右(个人的观点,在发达国家自闭症被高估了,而面盲症被低估了)。需要特别指出的,最极端的自闭症依然是自闭症,但是最极端的面盲症很可能不再被当作面盲症了,而是被当作完全缺乏认知能力的白痴或者有癔症的疯子了。
我的结论很简单,面盲症并不是严重的认知缺陷,但是研究它有助于帮助理解自闭症谱系中一个很重要的子集。面盲症和自闭症是人类认知能力进化的一个副产品,而不是一种基因突变。为了更好地干预(以及将来可能的基因疗法)自闭症患者,我们需要对整个谱系进行研究,而不应该用一种过于简化的还原论观点来看待(用 Prigogine 的话来说,需要在统计层次上进行思考,而不是从个体上思考)。
我第一次读到 On Intelligence 的时候特别兴奋。虽然我早就知道这本书但是却没有深究,不过这也是件好事,那时候 Jeff Hawkins 还只有直觉和理论框架,没有实际的数学模型和工程实现。我不想言过其实地夸大他所取得的成就,仅逐字引用我过去的读书笔记:
如果 Jeff Hawkins 是对的,新皮层能解决的问题是严重受限的,也难怪现代科学依赖符号系统和书写系统。新皮层的 False Postive 倾向也许是迷信的生理基础。正是因为新皮层的预测引擎试图解释一切,概率理论和量子力学才会显得如此的晦涩。
但是 Jeff Hawkins 也可能是错的,新皮层的自反馈系统以及和老系统的整合也许更加重要。在他的模型和实现中,没有出现情绪调节和所指。多巴胺等递质对智能系统的调整是如何实现的?自我认知和更复杂的意向层级是如何实现的?是否能具备语言能力和符号计算只是跟新皮层的规模有关,还是涉及到新的基因或特殊的蛋白质?
Jeff Hawkins 太酷了,仅仅是在提出有价值的问题上就已经是跨时代的。更何况他还把这些理论变成了工作系统,并付诸实践。也许在 Numenta 工作的基础上,上述的很多困惑都会得到解答。
不过我不打算讨论 Jeff Hawkins 的认知理论,而仅仅讨论 SDR,因为它非常简单可以直接做理论计算,而且对它进行定量分析也非常容易。我用 Mathematica 做了一些简单的符号计算和数值计算,还用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数据源做了一些数据实验,重现了 Jeff Hawkins 的大多数结论(当然我的目的和 Jeff Hawkins 完全不同,我还对它做了一些改良)。有兴趣的人可以去读论文或者进行计算,我需要提醒的是 Wikipedia 上的误差近似公式是错的。
Jeff Hawkins 通过 SDR 回答了一个计算神经网络无法回答的问题:如何在一个有噪声的环境下进行相对可靠的存储和计算。人类的感知系统非常糟糕,否则不会有所谓的 Hi-Fi 工业不停地骗钱;人类的硬件(准确的说是 wetware)很不可靠,神经元随时可能会失效,而且脑细胞不停地会死掉。但是大多数人的认知能力都很正常,有些人被子弹击穿头部都能正常生活(你可以试试拔掉一个内存条或者射击一下硬盘,后果自负哦)。SDR 作为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数据结构,却可以重现人脑的这些性质。满足一些条件(请参考原始论文),SDR 可以承受很高的内源性噪声,即数据结构本身出现了错误,同时可以精确地识别模式;SDR 可以承受很高的外源性噪声,只使用信号中的部分特征就能可靠的识别模式。我不是一个单纯的还原论者,所以我并不是想说人的大脑神经组成的网络是个 SDR 或者基于它的 HTM,而是建议:SDR 是理解人类认知能力的一个最小化的概念模型。
SDR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超参数(hyper-parameter),也就是使用输入信号的多少信息进行计算。这个超参数是离散的,但是为了方便讨论,我假设它是一个连续量。如果无视输入信号的任何信息,或者说使用 0% 的信息,那么这个 SDR 是平凡的完全没有用的,因为它的结论跟输入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使用信号的所有信息,或者说使用 100% 的信息,那么这个 SDR 也没啥用,因为它要求噪声也被匹配(这时候它等价于 Bloom-Filter,对于无损的计算环境而言,软件工程师们兴奋地宣布它没有 False Positive)。如果要精确,那么这个比例应该尽可能高;但是由于噪声的存在,这个比例高到一定程度就会让 SDR 变得过于“挑剔”。我先假定存在一个基因型控制了这个超参数(这个假设肯定是错的,但是并不阻碍这个思想实验),那么由于进化的存在,这个超参数一定会在合理的范围内,所以我们的祖先能够比较迷信地幸存下来(所以我们会有祭司和宗教,这是个必要的代价)。但是在这个合理范围的边界上,就出现了一些比较奇怪的个体。面盲症就是那些在合理范围内尽可能使用较少信息进行预测的个体,这些人倾向于认为万事万物都存在联系,善于总结规律成为呼风唤雨的神棍,在自然环境中可能并没有优势,但是在社会环境中就未必是坏事了;自闭症就是那些在合理范围内尽可能使用较多信息进行预测的个体,这些人善于观察细节并且可能宣称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虽然他们很可能更加精确和更少犯错误,但是他们的学习能力和社交能力受到了严重干扰,对于独立特行的猛兽未必是坏事,但是对于人类这样的社会生物来说是灾难性的。
我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仅仅看了 Jeff Hawkins 的一本书,就联想到可能跟自闭症和面盲症有关系,然后杜撰了这么一大堆文本。我们的认知能力并不是有一个或者几个基因所确定的,而是由一个复杂的基因调控网络所影响的,跟我们的生长、发育环境也有关系。就连我的自闭症有害假说都可能是错的,也许在大草原上,一个高冷独立特行的男性猎人更容易传播基因。我得坦白,如果有人能拿出一个更有说服力的概念模型或者计算系统,我会是那些最兴奋最高兴的人之一。
对于人类的认知机制和相关的缺陷而言,SDR 肯定是过于简化的模型。我第一天看到 Jeff Hawkins 的 HTM 的时候,就断言 HTM 实在是过于简化了。但是概念模型的价值正是在于其简单有用,毕竟我们都是还原论教育训练出来的灵长目动物,我们的直觉无法处理过于复杂的模型(比如狄拉克方程)。还原论和简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盲目乐观的原教旨主义者。
我使用超参数来描述一个控制 False Positive 的控制参量,那么很自然的问题是,这个超参数是否能调整?我怀疑在发育过程中,这个超参数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也许存在一个自适应的基因调控机制来帮助人类的幼儿学习语言和社交技能,因此婴幼儿可以发展出母语优势,并尽快适应社会生活(对于史前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可能更大)。
是否可以用药物来调整这个超参数?目前看起来是很困难的,虽然在另外一类认知障碍中,药物是有效的。在卡尔萨根的宇宙一书中,萨根提到了双向躁狂症,患者的情绪在极度悲观的抑郁和无所不能的狂躁之间振荡,用锂化合物就能缓解症状(Lithium (medication))。情绪是由神经递质所调控的,比如多巴胺和血清素,而不是由神经元连接的活跃数量所激活的。即便我们能找到方法来影响这个超参数,其效果也需要很长的时间生效,而且很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仅从数学模型和计算上,我证明了 SDR 可以被推到极限。在没有噪声的情况下,可以设计出性质优异的 Polymorphic SDR,其超参数是可以动态采样调整的。作为数据结构,SDR 之间是可以直接进行计算的,或者说 SDR 可以是兼容的。但是,对于两个不同人的神经结构,大脑皮层的空间结构是由基因和环境所决定的,其编码规则(或者说语义)几乎必然是不同的,换句话说它们是不兼容的。因此,即便有可能通过扫描人脑结构提取神经树突中编码的信息,我们也没办法直接把这些信息直接转移到另一个人的脑中(只要你相信 SDR,请忘掉一个神经元对应一个实体或者概念的假说吧)。我怀疑,上述过程甚至对于同卵双胞胎都是不可能的。我甚至只能悲观地断言,除非按照一定的保真度复制整个大脑结构,我们不可能有效地重现某个人的高级认知功能(比如记忆)。
说句题外话,虽然 Jeff Hawkins 在工程中使用的 SDR 具有非常严格的数学定义和计算模型,但是仅从字面上来说,大脑神经网络几乎天然地具备稀疏性(Sparsity)和分布性(Distributivity)。现在非常流行的 Deep Neural Network 也是基于 Distributed Representation 的。不过,想要理解这些概念的意义,可能需要具备相应的计算数学背景。
我一直怀疑自己有轻度的 Bipolar Disorder,但是大概是另一个 false positive。但是我受到周期性的 Imposter Syndrome 影响,不定期地会感觉到自己是个骗子,智商非常低(跟学术界的顶尖玩家比起来,这是残酷的事实)。在这个阶段,我会喜欢听各种无病呻吟的摇滚乐,看怀旧电影和美剧,偶尔会有写小说的冲动。有几年我非常厌恶这种状态,妄想通过加班或者做家务来熬过去。最终我接受了自己,假装自己是个困在人类大脑里面的外星人(Teaser: My alias is an alien from Futurama),安慰自己必须容忍这些 wetware 的缺陷。我发觉看看美剧没什么坏处,《真探》里面 Cole 的形象让我感觉到自己还是个心理相当正常和积极的人:
我很少看反复地看同一部美剧,但是我至少看了三遍囚徒 (豆瓣)。Dreamer 这个设定实在是太酷了,但是成为 Dreamer 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我们当然可以假装每个自闭症患者在自己的内心中有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但是我们也需要面对现实,就像男主角那样做出最终的判断。
有时候,尤其是在受到挫折的时候,我也想退缩到墙角,像 Numb3rs 的男主角那样躲在地下室里研究 NP=P 这样的问题,不去跟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打交道。每个人都需要自己的私人空间和逃避的可能性。但是我们毕竟是社会动物,失去了社交技能很难独立生活。
所以,研究自闭症就是在研究我们自己的认知极限,帮助自闭症儿童就是在帮助这个社会。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可能超越自私的基因的束缚,去面对存在的荒谬,想象和构建一个更好的社会。引用 Ilya Prigogine 的话作为结束语:
我并不是自闭症的研究者,我的身边也没有长期追踪的案例,请不要把我这里提出的猜想当作实证的科研结果。即便在将来,这个猜想得到了部分证实,它也仅仅对狭义的自闭症定义有效。此外,我对自闭症的理解来自于互联网上零碎的信息和耶鲁大学的公开课:
我建议对自闭症和认知科学有兴趣的读者看看这个公开课。另外,我需要强调一下,不要因为对自闭症了解就认为自己可以做自闭症的诊断,请参考实际的诊断手册并且找专业人士介入。如果有可能,患儿的家长最好去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做诊断和干预治疗。请不要把确诊的自闭症患儿当作普通孩子来关怀和教育,这是错误的并且可能会耽误干预。由于自闭症跟认知发育相关存在一个有限的时间窗口,患儿的家长有必要自己去了解相关的前沿知识和干预方案。请相信专业人士,因为这是目前的技术条件下最好的选择:
欢迎转载或者在此基础上做任意的演绎——如果这有助于社会对自闭症的了解。但是请注意我并没有任何图片的版权或者授权,我会不做任何通知地编辑、删改原文,我也不会承担任何连带的责任。作为匿名的代价,我不会关心署名权或者 Credit。
自闭症,之所以,在中国残联被翻译为“孤独症”,就是因为普通人会将其与“抑郁与自闭”心理问题混为一谈。
所以,自闭症的定义中最重要的一点是:Autism孤独症,是一种儿童发展障碍。根本不存在成人在家呆久了。。。就变成孤独症这样的疑惑。
版权声明:本文为 “小儿收惊网,小儿辟邪小儿化煞宝宝平安符小化化病小儿夜啼符小儿聪慧符” 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 留言与评论(共有 条评论) |